新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引入国企股东西安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20亿,注册资本由33.3亿元增加至53.24亿元,媒体将之概括为“国资出手”。
但马上就爆出,三大民营股东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增资权,提起多起诉讼维权,索赔金额高达19亿。
为何民营股东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增资义务,却又失去了增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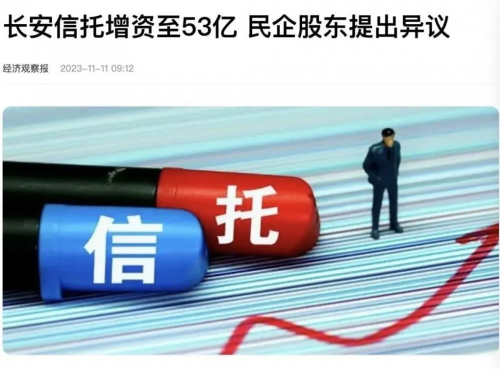
(图片来源于网络)
根据新闻报道,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下发《监管强制措施决定书》,认为民营股东未如实报告一致行动人及关联关系,也未如期完成整改,因此限制其参与长安信托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包括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增资权。
还有一个争议点是股权作价问题。据悉,长安信托选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做增资专项审计,审计结果为公司净资产33.85亿元,而一个多月前希格玛为长安信托出具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列明的净资产为76.88亿元,少了43亿。而后按照专项审计的评估价,长安信托完成20亿增资,国企新股东西安财金入局。
假设没有陕西监管局的一纸决定,长安信托今日之股权结构必然大不同。
在金融强监管之下,陕西监管局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合理?成为了股权之争的关键
01
如何看待金融监管
监管的本质,是“要求与限制”。
金融监管从法律上而言,确凿无疑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其中监管机构为行政主体,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对象,为行政相对人,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天然不平等,一强一弱。
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将成为我国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金融监管领域的行政力量将愈发强势。
但即便如此,行政法治仍然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基本准则。
行政监管应具有合法性与可预期性,首先体现为“有法可依”,其次为“依法行政”。比如有没有一个事先宣布的规则?政府的行动是否遵循了这些规则?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有着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但具体执法层面,尚需依赖大量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其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法律解释,乃至司法审查的问题。
比如金融监管中对于股东权利的限制问题,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于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控股股东,监管机构可以采取“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如果不是控股股东的,字面上的规定仅是“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具体是指什么权利?能限制到什么程度?是存在一定解释空间的。
《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其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可以限制信托公司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包括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但此处的“相关权利”作何解释?“处分权”的内涵有哪些?“等”字如何解释,是否包括限制股东增资的权利?
——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在精确性与可解释之间,会存在争议/解释空间,这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呼吸阀门,也可能成为某种黑暗洞穴。
02
金融监管的尺度:比例原则
在模糊与争议地带讨论金融监管的尺度,最重要的莫过于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可谓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
比例原则最早出现于警察行政领域,“若有多种方法足以维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御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险,则警察机关得选择其中一种,惟警察机关应尽可能选择对关系人与一般大众造成损害最小方法为之。”(参见1931年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第14条规定)。
后来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比例原则超越警察法领域,直至成为许多国家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其核心内容是行政成本应与行政效果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法谚有“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以及古语云“杀鸡焉用牛刀”。
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其内涵包含:
1. 适当。所采取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这是一个“目的导向”的要求,以金融监管为例,不论是强监管还是弱监管,都须有正当的目的,且有助于监管目的之实现。
2. 必要。在能达成行政目的的多种方式中,应选择对相对人最小侵害的方式。这是比例原则中非常核心的内容,是从“法律后果”上来规范行政目的与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
3. 均衡。行政行为的实施应当衡量其目的所达到的利益与侵害相对人的权益,两者孰轻孰重,只有前者重于后者,其行为才有合理性。在金融监管中,如果存在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须用雷霆之手段,才能挽大厦于将倾,那么所采取的措施则符合比例性原则。当然,“何轻何重”、“何为适当”,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
简言之,三项子原则分别从“目的取向”、“法律后果”、“价值取向”上规范行政权力与其行使之间的比例关系,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构成了比例原则完整而丰富的内涵。
03
如何用比例原则评价金融监管行为
比例原则是建立在合法原则基础上对金融监管行为的进一步研判,既考虑监管目的,又分析监管手段。
具体而言,监管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监管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对被监管机构及其股东的权益影响程度如何?可否采取其他替代手段?采取这样的监管措施保护了哪些利益,将损害哪些利益?以及整体利益乃至法益上的衡量?
按照比例原则来思考,第一步要考虑的是监管目的。
如果金融监管措施实施之目的实为排挤一些股东,甚至配合做低净资产以让另一些股东低成本入局,则显然不再具备目的上的正当性。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违反监管的是国企股东,跟民企股东是否会有不同对待?仅就这一点思考,就又会回到法治本身的争论——平等对待,不看身份/不差别对待,乃法治的基本原则。
当然,如果金融机构及其股东的确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已造成金融风险的重大隐患,那么无论其股东身份是国企亦或民企,对其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乃至清-退出局就具备了目的上的正当性。
第二步考虑的是“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做了什么?违反了哪条规定?”即错在哪里?错有多大?
这就不可避免涉及事实认定。张庭林瑞阳名下达威尔公司涉网络传销被石家庄某区市场监管局调查一案,在听证会上,律师团凭借计算机及法律专业背景,揭示涉案鉴定报告中电子数据MD5校验值系伪造的重大事实,行政机关认定所依赖的核心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彻底坍塌。关于事实的认定(举证),犹如地基。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是归属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在做出监管措施时,就要有足够扎实的“定案证据”;但被监管对象欲证明监管措施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亦须组织起足够的反驳证据。
第三步,再论“对应采取何种监管措施?所采取的措施是否与其错误/违法之处匹配?是否足以使其纠正错误?”
如果是持股比例超额,要求其转让股权即可;如涉董事名额的问题,剥夺其提名权即可;如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责令其进行信息披露即可。总之,过罚相当。
第四步,可再深入思考,采取这样的监管措施保护了谁的利益?侵害了谁的利益?是否最大程度上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是否动摇了公司自治?等等。
按照比例原则,这几层思考是层层递进的——需目的性正当、措施得当,法律效果良好。
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法治。
市场主体会很快意识到,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私法,是其他的竞争者与合作者,还有公法——尤其是政府。
每个政府当然必须有所行动,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这种情况下,政府及其部门在一切行动中受到事先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跟市场主体遵规守矩、秉承诚实信用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没有法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